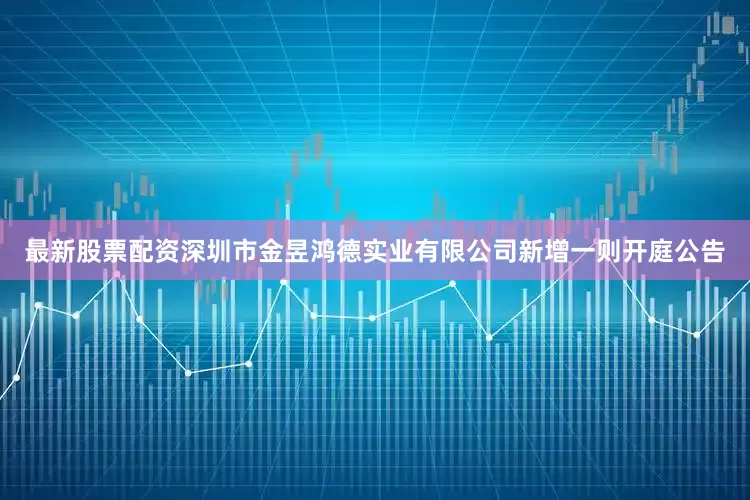1946年秋,华北战场上,解放军刚刚遭遇了成立以来最惨痛的失败之一:精心布设的“围点打援”战术彻底失灵,不仅没能消灭敌援军,反倒丢失了战略重镇张家口,部队伤亡五万多人。傅作义的一封公开电报,更是像在伤口上撒盐,极尽嘲讽之能事。究竟是怎样一支部队,能让初期的解放军栽下如此大跟头,并逼得他们两年后完成一次彻底的蜕变?
大同、集宁的失利,对当时的华北野战军来说,不只是丢了几座城那么简单。那是一次迎头痛击,把所有人的傲气和信心都打进了泥里。要知道,当时解放军的设想很美好:围住大同,吸引傅作义的部队来救,然后一口吃掉。
这叫“围点打援”,是拿手好戏。可结果呢?援军没打着,自己的后院先起了火。张家口丢了,解放区被拦腰斩断。部队伤亡五万多人,代价惨重。

傅作义那封极尽嘲讽的电报,就像在伤口上撒了一大把盐。它不仅刺痛了前线的战士,更让整个解放区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和耻辱。
这股气,憋得人喘不过来。傅作义不是蒋介石手下那帮只认武器、不懂变通的嫡系将领。他用兵,又刁又狠。抗战时,日本人就领教过他的厉害,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七路半”,意思是比八路军还难缠。
当中央军委布下大同这个口袋阵,等着敌人钻进来时,傅作义就像个老辣的棋手,一眼就看穿了棋盘上的杀机。蒋介石催他去救大同,他嘴上答应,人却根本没动。他连夜开会,手指敲在地图上另一个地方:集宁。
那是解放军的后方,张家口的门户,兵力空虚。不去硬碰硬地解围,而是掏你的心窝子。这一招“围魏救赵”,瞬间就让战场攻守易势,把主动的解放军,活活从猎人拖成了猎物。
他手下的董其武,带着三万精兵,像一把烧红的刀子切黄油一样,四天就捅到了集宁城下。这种速度和决断,背后就是傅作义的影子。
如果说傅作义的脑子是这支部队的灵魂,那他手下士兵的筋骨,就是钢铁铸的。集宁城下,解放军一度以为胜券在握。他们设下圈套,想诱董其武的部队进城,来个关门打狗。

计划是好计划,但执行出了岔子。负责协同的几支部队,因为种种原因,晚到了整整十个小时。就这十个小时,董其武的部队硬是把一座近乎空城的集宁,变成了钢筋水泥的堡垒。
他们纪律严明得像一部机器,而且有一种近乎野蛮的顽强。老兵回忆,傅作义的兵,打起仗来就是不要命。亲眼看着一个敌人中弹倒地,血流了一片,都以为他死透了。可一转眼,那人又挣扎着爬起来,端着枪继续往前冲。
这种亡命徒式的打法,让习惯了打运动战的解放军极不适应。他们就像一群疯狗,咬住了就死不松口。这股狠劲儿,是许多养尊处优的国民党部队根本不具备的。
傅作义的部队里,装备着一种英国造的斯登冲锋枪。这枪有个致命的设计缺陷:枪管太薄,连续射击后极易过热。滚烫的枪管,甚至能把射出去的子弹都熔化。
被这种子弹打中,伤口根本不是一个窟窿,而是一团模糊的血肉,创面极大,极难处理,感染率奇高。许多解放军战士因此被迫截肢,痛苦不堪。

这种武器给对手造成的心理阴影是巨大的。但反过来看,使用这种武器的傅作义部队,自己又何尝不是在和死神跳舞?一把随时可能出故障、甚至伤到自己的枪,却被他们用成了令人生畏的杀器。
这恰恰证明了这支部队的另一面:他们不仅对敌人狠,对自己更狠。连这样残酷的装备缺陷都能克服,并转化为一种震慑力,可见其内部的训练强度和精神韧性,已经到了何种地步。
大同、集宁的惨败,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年轻的华北野战军身上所有的问题。战后总结会上,聂荣臻元帅第一个站出来检讨,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。他坦承,所有人都“低估了傅作义”。
问题是明摆着的:各解放区部队临时凑在一起,指挥不统一,配合一团糟,打起仗来各行其是。习惯了游击战,突然要打大规模的攻坚战,经验和火力都跟不上。面对大同那样的坚城,只能干瞪眼。

失败是痛苦的,但解放军最强大的能力,恰恰是在失败中学习。这次惨痛的教训,逼着华北野战军刮骨疗毒。他们重整指挥体系,加强协同作战,专门研究克制傅作义部队的战术。
两年后,1948年8月,解放军兵锋再临,一举收复张家口,洗刷了当年的耻辱。又过了四个月,聂荣臻与林彪率领华北、东北两大野战军,将傅作义的部队团团围困在平津地区。
这一次,那个曾经写信嘲讽毛泽东的傅作义,选择了起义,亲手为北平的和平解放拉开了大幕。傅作义和他的部队,是解放战争初期一块最硬的磨刀石。他们是解放军最可敬,也是最残忍的教官。
顺阳网-线上股票配资公司-东莞配资平台-教你如何买入卖出股票的方法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